季風書園:文化大革命的頭髮去哪兒了
- Yue Wu

- Nov 5, 2025
- 22 min read
受何流邀請,錄製季風書園podcast,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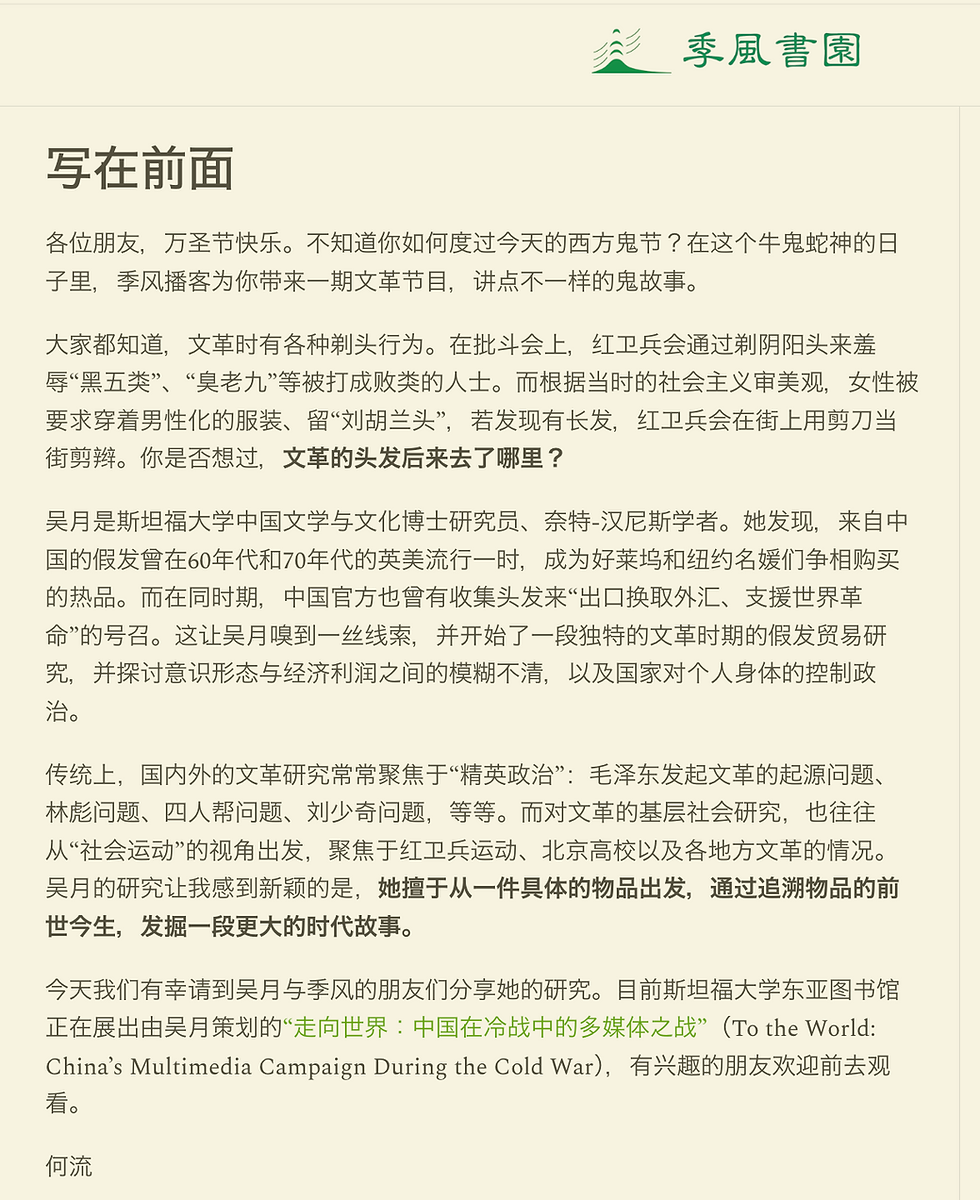


许多关于美国发型史的研究指出,蜂窝头之所以在六十年代突然流行,是因为在此之前人们使用的假发大多来自欧洲,价格昂贵,只有少数人能负担得起。而六十年代之后,出现了一批廉价且质量上乘的亚洲假发,尤其是由亚洲头发制成的产品进入了美国市场,使得普通女孩也能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戴上像好莱坞明星一样的蜂窝头发型。
于是,一个有趣的画面出现了:
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在革命理想的感召下,将头发捐给国家,说要“支持世界革命”;而这些从身体上割舍下来的头发,却通过国际贸易流转,最终成为了西方摩登女孩的美丽装饰。
她们都是所谓的摩登女孩、现代女性,但她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经历都是如此不同。这样的两条平行线相互对照,让我认为很讽刺、很感慨,也因此想要把“谎言”作为我的研究核心。

一个装着头发的信封和它背后的历史谎言
H:你之前做了关于文革大字报的研究,最近又在研究文革时期的头发,这两个方向都非常新颖。你从具体的物件出发,去追溯它的历史,展开关于文革、关于时代、关于中国历史的叙事。你一开始是怎么开始关注到在文革期间的头发贸易这个议题的?
W:当时我刚到斯坦福。因为我之前比较喜欢做和艺术相关的工作,就想找一找有没有策展的机会。于是我去了学院、图书馆,和那里的老师、馆员聊天,介绍自己。
我注意到图书馆里有一个常年轮换的展览区,所以跟他们说,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也希望能参与。后来机会很快就来了。
他们当时正好有一批收藏,是冷战时期的主题材料。斯坦福东亚图书馆的Xue Zhaohui老师,多年来一直在收集不同主题的文献和物件。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世界革命”的,可以看到像“亚非拉团结”、“反帝反修”这样的口号。
当时我的工作,就是对“世界革命”这一批材料做整理、筛选,包括几百本早期出版物、各种小物件,全都堆在一个满是灰尘的办公室里。就是在那样整理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了一个小信封。
当时觉得很奇怪,仔细一看,才发现那是一个用来收集头发的信封。信封上画着一艘大型货轮,航行在海平面上,背景是日出或落日。上面写着“回收头发,支持世界革命”。
看到这样的东西以后,我的好奇心一下子被激发了。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才走上了后面这一系列探索的道路。
H:当你拿到这个信封的时候,你的直觉是什么?有没有一种预感,好像这背后藏着什么故事?
W:直觉当然是很奇怪。首先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存在”、这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怎么做到的?也就是最基本的三个问题:What、Why、How。光是这三个问题,就已经让我认为这个现象值得深入去探一探。
当时我刚好在上历史课,课题的时间范围也差不多,是关于整个东亚的近代史,侧重讲韩国和日本,关注的是几个国家之间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交流。我就把这个信封拿给当时的历史系教授 Yumi Moon看,跟她说:“反正我得写一篇期末论文,那我写这个信封怎么样?”
她一看到就特别兴奋,说:“哇,这个太棒了,太棒了!”我当时印象很深,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当教授真的觉得你的选题好的时候,她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一刻我认为“有戏”。
在研究过程中,我的视角不断切换,最后落点放在了“谎言”这一主题上。我的目的并不是单纯揭示当时存在这样一种头发贸易,而是想探讨这种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冲突。
研究中最具张力、也最能与当下产生共鸣的部分,是这种矛盾:国家号召民众为了“世界革命”剪掉头发、回收头发,以此象征对理想的奉献与服从。但在国家层面,这些被回收的头发却被出口、卖给他国,成为装饰品。
这种行为本身是一种背叛:一边颂扬理想,要求民众去服从;
另一边却在以“革命”的名义进行欺骗与牟利。
冷战禁令下,美国为什么默许这场头发交易?
H: 按理说,当时美国在冷战期间对中国是实行禁运的,可与此同时,又发生了这样规模庞大、持续多年的贸易。美国为什么会让这件事发生呢?
W:我参考了另一位专门研究冷战期间的“中国头发”(communist hair)的学者 。当时美国其实是禁止使用这些头发的,因为其中涉及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国家之间的政治对抗。
但是这位学者发现,作为中转站的香港仍然要做生意。政治话语是一方面,现实生活又是另外一个层面。虽然理论上全面禁止进口 communist hair,但香港的中间商把中国来的头发标成来自印度尼西亚,换了一个名头,再重新出口到美国。
如果这些头发真的都来自印度尼西亚,那么为了满足市场需求,需要多少女性在一年里长出足够的头发量?这个数字根本不可能达到。实际上大量头发是来自中国的,只是被换了一个名字出口了。
这样的案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官方有禁令,而现实中,为了生计、为了操作,底层的人总会找到自己的应对办法。
H:就像今天美国给中国贴一个关税,越南和美国的贸易就突然暴涨,或者美国禁止出口 GPU(图形处理器),然后新加坡的订单就突然暴涨。
W:我之所以认为“谎言”是最有趣的地方,也是因为类似的历史在当下也有回响。类似的行为方式,一直都在被延续。

《白毛女》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样板戏之一,讲述农村少女喜儿受地主迫害、白发沾身,最终在共产党帮助下获得解放的革命题材故事。/Wikimedia Commons
白毛女,是女鬼还是战士?
H:我们团队在探讨这期节目时,都认为这不太像真实世界的事情,更像是鬼神世界的情节。你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有没有某一刻让你觉得,原来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
W:有。我进行研究时,一直在思考样板戏《白毛女》里的白毛女形象和她的发型。
当时整个社会里,大部分女孩都是刘胡兰式短发,要么扎辫子,很少有人披头散发。而在舞台上,样板戏融入了芭蕾舞元素,女性第一次可以打开身体,做一些以前传统里被认为过于奔放的动作。白毛女一边劈叉等动作,身体姿态优美,伴随着她飘动的白发,我试着想象这一幕在当时的视觉冲击力,那种场景会让观众感到多么震撼,一个美丽的“女鬼”。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场景让我联想到圣经宗教画里的 Mary Magdalene,她是耶稣的信徒,同时也是女乞丐,非常贫穷。她的形象被塑造成衣不蔽体,但用长发遮住身体部分。在宗教画里,她既是虔诚的宗教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可以被性化的课题形象。
白毛女是否也带有类似的性隐喻或者视觉刺激?但我和其他学者讨论时,有人并不同意,而认为白毛女其实是一个反抗者。但这种反抗并不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进行的,而更像是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形象。要进行反抗,你不能保持普通状态,而是必须达到一种非人的状态。反抗之后,她最终被八路军重新收编,才被“合理化”。
H:这跟性欲的隐喻也不矛盾啊。她被收编也可以带有性意的隐喻。
W:但对白毛女的核心解读,仍然涉及统治的问题。在统治的逻辑下,如果要真正出格地完成革命反抗——当时土改要求的反抗地主,作为一个贫农,必须以一种非人的、妖魔化的状态去斗争。最终,她仍然需要由正统的八路军或其他正统革命者来“解救”,以使她的行为被社会所接受。
头发在中国作为“服从”的代言
H:你怎么看头发的含义?这个东西好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我能想到历史上类似的例子,比如清朝时期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削发令。现在,中国的学校似乎也一直对学生的外貌有严格要求。女生要留特定发型,男生也有规定,每个人都要穿校服,有很多限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对头发和外表的管控在历史上就一直存在。
W:这里我只能借用福柯关于 biopolitics(生命政治) 的概念。大意是,在现代社会之前,这种权力被称作 sovereign power(主权权力),它的核心是决定谁生谁死。无论是君主还是皇帝,他们拥有生杀大权,这是非常野蛮、血腥的权力。
福柯认为,进入所谓的文明社会后,这种“决定谁去死”的权利需要被重新思考。因为另一种权力形式产生了,也就是 biopolitics。如果说 sovereign power 是 let die,让人去死。biopolitics 是 make live,让生命延续。它关心的不只是个人的生存,也关注整个社会、群体的繁荣和延续,是以“生”为核心的权力统治和管控。
比如说,为什么会有优生优育、计划生育,以及各种教育选择?目的都是希望这个群体里的每个人都能服从、听话,成为“优秀的公民”。
不仅仅是头发,它也可以是你的外貌、衣着、说话方式,以及对社会规范的遵循。头发只是其中之一,但它体现了权力如何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身体的每一个细节进行规定。
当时,中国女性削发并不是单纯为了革命,也是因为留长发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小资象征,是社会规范所批判的行为。她们被要求舍弃个人对美、外貌的追求,成为革命女性、新女性。讽刺的是,她们舍弃的头发最终却成为西方现代女性追求美和自由的象征。
福柯认为,相比以往 sovereign power 的血腥和暴力,biopolitics 是文明社会权力的象征,是一种相对“进步”的权力形式。但后来的一些理论家,比如阿甘本等,就指出这种权力同样“野蛮”。它对每个人的行为习惯进行全面管理,无孔不入,可能引发新的控制和压迫。比如头发,对身体最小部分的控制;在 COVID 疫情期间发生的各种现象,也理解为 biopolitics 的无孔不入。
H:有了生命政治之后,也不代表国家就不杀人了。比如文革时期,仍然有人被迫害致死但对身体的管控一直都很强力,两者其实是同时存在的。所谓的“野蛮”和“文明”,并不是直接替换的关系。
为什么国家如此在乎对个人身体的控制?
H:我前两天在读一本师大女附中学生的文革回忆录,里面讲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时候,学校里女生是可以穿裙子的,也有人扎辫子。但到了六十年代初,学校开始说,一个辫子是帝国主义,两个辫子是资本主义。于是女生们就必须把头发剪成“刘胡兰式”的革命短发,重新学习毛主义,也不能化妆。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共产主义的身体控制并不是从 1949 年那一天就完全开始的。在你看来,为什么国家如此在乎个人的身体?它保持对暴力的垄断,不就已经掌握了统治吗?为什么这种权力必须延伸到身体、头发、血液,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W:国家不可能像以前的 sovereign power 那样随意决定谁生谁死。虽然极端情况下还是有一些例子,但大部分时间,并不能随意处置生死。
对身体的控制,恰恰是为了让人服从。这是一种服从性测试:从最细微的地方开始。比如孩子必须穿校服,每个人的穿着、发型都有规范。如果所有人都习惯了高度纪律化的生活,严格遵守各种规范,那么这一群人自然更容易被管理和统治。
H:为什么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开始犹豫使用更加直接、明显、手段狠毒的暴力?在我看来,国家完全可以把不喜欢的人关起来,而且确实关了很多人。文革时期有劳改营,也有各种手段把人隔绝起来。
在这些基础之上,为什么国家还认为自己需要去管理头发?为什么这种权力要延伸到生活的每一个微小细节?
W:你觉得哪一种更有效?
抓人送进集中营是抓不完的,这需要巨大的财力和人力。要let die,其实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相反,如果国家选择 make live,通过对身体和日常生活的管控,把人塑造成它理想中的样子,一方面可以保证一种“繁荣兴盛”的景象,另一方面不再有必要频繁地去 let die。
我为什么把大字报作为视觉艺术研究?
H:你能不能讲讲你的大字报的这个研究?
W:当时在哈佛费振清研究中心有一个大字报展览,空间本来也不是专门用来做展览的。原本那里还有一张乒乓球桌,后来他们把乒乓球桌上的网拆掉,把桌面平铺开来,变成一个横向的展柜。那个地方以前主要是大家聚会的空间,但临时改造之后,就成为了展览的一部分。
像毕业季的时候,展览空间上贴的都是那一届毕业生的照片。这个空间完全不同于任何正式展览场地,它非常生活化。当他们把空间改成展厅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非常震撼的,因为我从未真正见过任何一张大字报,只在网上看过图片。
这些大字报有的两三米高,比我还要高。像研究纽约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家Jackson Pollock时常用的形容词“size matters”,强调作品的巨大尺寸会带来沉浸感和视觉冲击。我第一次踏入这个空间时就感受到了类似的震撼。整张乒乓球桌上摆满了比桌面还要大的大字报,还需拼接其他部分才能完整呈现。我拍照时都得垫脚才能拍全,这些文字像排山倒海般呈现在眼前,视觉冲击非常深刻。

1967年10月,大寨军民斗私批修大字报/Wikimedia Commons
在展览期间的一个panel上,我的导师田晓菲教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现场没有人意识到其中的不合理性。他拿出一张历史照片,一栋五六层高的楼里,许多年轻人搭梯子贴大字报。他问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张照片里有什么奇怪的地方?”现场很安静。最后,麦克法夸尔教授回答:“贴到这么高的地方,没有人可以看清字写的内容。字太小,站在地面根本看不见。那么贴它的意义在哪里?”
那一刻我意识到,这正是大字报的关键:它的视觉冲击力本身,而不是文字内容。内容无非是毛的语录或支持、反对的信息,大同小异,但它通过视觉呈现营造出一种集体意识。对于支持者,它是一种团结和认同;对于被批斗者,它是一种压迫。
这也让我思考是否可以将大字报作为研究主体,而不是辅助手段。大字报不仅记录了批斗对象或事件,它本身是否推动了文革的发生。例如,最初北大的食堂贴出聂元梓的大字报,随后毛的出现。
后来形成两种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单位和工厂强制写大字报,干部一天二十张,普通群众一天六七张,小学生也被要求完成;另一种是自下而上,草根揭露。如文革晚期广东的李一哲大字报,以“批林批孔”作为标题,但标题下书写的是自己的反抗和不满,我用你的话语,来实现我的目的。
在斯坦福展览中也有类似例子,例如“批林批孔,反帝反修”的研凿机,但最后也要把机器做出来,完成科技进步。这显示大字报作为具体媒介的复杂性,通过它可以丰富我们对文革历史的理解。
H:而且你后来发现大字报本身后来变成了一种商品,被卖到还是被传递到海外?
W:这也是我后面要继续研究的方向。我知道胡佛研究所收藏有大字报,我去看时,他们告诉我不能直接看原件,只能提供电子版。
大字报像新闻一样,是快速被替代的媒介:
贴出来是为了被撕掉,每天都有大量新贴出来的旧大字报被覆盖,再被撕掉。
因此能够保存下来的非常少。哈佛展览里的一批大字报背后的故事也很有趣:它们原本是用来包陶瓷器的包装纸,一位外商在收到货后发现包装纸上写有文字,打开一看竟然是批斗的大字报,于是才得以被回收并最终用于展览。
胡佛把大字报保存得非常精致:将大字报以类似中国画的形式制作成卷轴,即便大字报纸质粗糙,也会裱在一种仿绸缎的背面。这种处理形式非常特别,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我必须亲眼看到实物,因为单凭照片无法感受这种保存方式的独特与奇异,是谁来做的这件事?
H:几乎是把它当做一种艺术品去对待。
W:我后来给胡佛研究所发了邮件咨询,他们的研究员回应非常有趣,“绝对不是我们。”但他们表示,如果我做这个研究,非常欢迎我和他们的conservators(文物修复专家)一起讨论。
实际上之前几乎没有人进入过他们的地下室,是恒温恒湿的环境,收藏条件非常专业。当时有两位修复专家陪同我,其中一位曾在大英博物馆工作过。我们戴着白手套,打开木盒子,里面装着四卷大字报,仔细查看里面的内容。
仔细观察这些材料可以发现,它们的装裱其实相当便宜。问题在于,这些卷轴究竟是有人随意挑选一些漂亮的字、简单装裱后卖给不懂的外国人,类似改革开放早期假文物出口,还是这些内容本身具有特别价值,所以有人决定以更精致的方式保存下来?这一点至今仍是一个疑问。
H:这些当年的物品在视觉上非常鲜明,比如大字报、文革时期的各种宣传海报,大红色的背景,醒目的文字,“打倒美帝国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画面中有红太阳、天安门、农民锄地等形象,都传递着非常明确的政治信号。在当时,这些物品承载着具体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意义。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亲历者再回头看这些物品,它们的意义可能发生了变化,带上了一种怀旧的情感。而对于他们的后代,比如我们这一代人,看到这些物品时,又会赋予它们新的解读。由此可见,这些历史物品在时间的洗刷之下,仿佛获得了新的生命,不断生成新的意义。
W:我很同意:这些物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我们的上一代人亲历了文革,在回溯这一历史时,也产生了艺术性的再创作。例如王广义创作了毛的肖像画,并在画面上加入可口可乐等符号;吴山专和谷文达则大量借用大字报的视觉体系,将其转化为艺术装置。如果我们去看他们早期的作品照片,就可以发现他们提炼了文革时期视觉元素,并将其重新组合,形成具有当代艺术特征的创作。
H: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新的作品呢?它们是否是一种危险的怀旧,对那个疯狂时代的追忆,甚至带有“为那个时代招魂”的意味?还是说,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反思,是对历史创伤的消化与处理,提醒我们避免过去的灾难再次重演?在进行这类创作的时候,这条界限显得非常模糊。
W:这不仅适用于创作,也同样适用于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创作者,总是要不断追问“意义”。就像童年的创伤会伴随你而存在,你并不一定需要立刻去“为它招魂”,也不一定要马上批判它,它往往只是存在于你的生活中,你需要与它共存,慢慢去理解。这个过程既漫长又痛苦。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者来说,也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小时候的这些记忆究竟对我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持续去追问、去研究、不断在这个方向上探索,或许最终,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答案。
时代距离和视觉冲击,文革为何吸引年轻一代?
H:其实我好奇,文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老一辈人来说,他们亲身经历了文革,自然有很多反思,也带有文革情结。但到了现在的年轻一代,研究文革似乎变成了一个相对冷门的话题。
W:有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时代?反而我认为,恰恰是因为距离感,我属于特别年轻的一代,文革仿佛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过去。正因为这种距离和陌生感,让我产生了很多好奇心。对我来说,这种研究反而很直观,我的历史其实学得很差,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研究方法一定要从具体的物件出发,这些物件让我感到不理解,也让我认为奇怪。
文革时期的视觉体系,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现代主义的设计和审美已经无处不在,成为一种常态,而文革时期的宣传画和毛时代的物件,虽然有部分民俗和劳动人民元素,但它们在视觉和精神层面上试图传递一种强大的理想力量。第一次接触时,我感到非常震撼。
我在策划这个展览的时候发现,很多美国学生对文革时代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会惊叹,“哇,这个展览好漂亮。”我认为这种距离感加上视觉上的冲击激发了好奇心,促使我们回溯到底发生了什么。再加上这是一个被遮蔽的历史,更让人想去解开其中的谜题。
此外,文革留下的痕迹,其实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中仍然存在。戴红领巾、做少先队员、班长、两条杠三条杠、入团、作业批改、小红花等等,很多制度都是那个时代延续下来的。它既有很大的距离感,像一个禁忌般不被触及,但又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H:你是否关注过一些外国学者对文革的研究,以及他们目前的研究方向和视角大致有哪些?
W:在西方,有很多不同的研究视角,本土学者往往难以建立某些联系。例如样板戏中所融入的芭蕾舞这一外来元素。若仅从批判文革的角度出发,很难看到其中的文化包容性或某种进步性。
例如 Julia Andrews 等学者在艺术史领域尝试寻找文革时期的美学价值,或者探讨能否将这些宣传画作为艺术品重新审视。这样的研究在文革研究中本就少见,在艺术史中也罕有。
文革时期的政治宣传画,其创作者多为匿名或集体创作,其作者性也被悬置,这使得重新审视这些作品成为可能,并在不同学科中开辟了全新的视角。
H:这让我好奇,目前从事纳粹视觉研究的学者是如何操作的。一方面,视觉原理可能与文革类似;另一方面,他们也面临相似的道德困境:如同文革,纳粹理应被全面否定,但在观察和理解其机制时,很难完全避免产生某种同情或理解。
W: 在道德上,我们可以全面否定某段历史或政治体制,但如果因此封闭或否定它的所有表现形式,就可能失去对其中机制,尤其是视觉系统的理解。比如,无论是中国阅兵,还是纳粹队列表演,都是通过消除个性、统一动作,创造震慑、敬畏甚至升华的视觉效果
历史研究一直有人在做,但每一次都会带来新的反思。那为什么我们却可以完全忽视其中如此突出的视觉系统?它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我们选择不去看见那些极具反差的画面,以及那个真实发生过的世界。
受害者还是压迫者?文革中的善恶模糊
H:我认为官方似乎想埋没这段历史,而经历过文革、全面否定文革的人,也往往不愿回忆或正视它。这段历史涉及许多人的亲身经历,大家都在批判文革,却很少有人承认自己当时的行为。
W:也有人指出,文革对知识分子当然是劫难,但他们恰恰掌握话语权,因此后来的回忆录和研究多出自这一群人,自然呈现负面声音。而对许多真正的普通农民来说,那段时期反而是“黄金时代”。
H: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并非如此简单。在文革中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多是五六十年代曾参与迫害的人,或者四十年代内战时期选择留下、为政权服务十余年的群体。最终大家似乎都将责任归于毛泽东,从而免除了对这些人的追责。
W:我曾读过一本对我影响很大的书,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课上我们只读了其中两章,但我很快读完了整本书,读到最后时泪如雨下。书扉页写着:“我是一个红卫兵,但我不后悔。”
读到描述武斗的部分时,那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年,为了理想开炮冲锋,彼此厮杀,最终牺牲。他们的生命既鲜活又短暂,历史不会记住,也不会歌颂他们。
H:我两年前离开中国前,回了一趟老家,宁夏和甘肃。在宁夏的父亲家,我是回族。我问村里人文革时期“养猪”的事,他们说当时清真寺被改成猪圈,每户回民家里都有猪圈,唯独一户没有,因为那家人是红卫兵,负责监督其他人。
回到甘肃的姥爷家,他们家祖上在清朝曾是地方官,留下整套官服和配饰。文革时,隔壁家来批斗,把官服拿走;家里的土地也被分割。直到今天,那些邻居依然在附近。
思考这些故事,我就在想:谁是受害者,谁是压迫者?表面上,红卫兵是压迫者,其他农民是受害者;我家是受害者,对面邻居是压迫者。但他们自己会这么看吗?也许他们自认为是受害者,只是被另一种权力格局压迫。
在文革这个复杂世界里,责任到底该由谁承担?
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场看似无数人参与的政治灾难?
W:这就是洗脑的作用。如今的孩子,如果沉浸在某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中,可能会真心认为自己在做对的事,为理想行事,却违背普世的人性,去伤害他人。
在研究过程中,我也开始重新审视“绝对善”、“绝对恶”的观念,这种划分似乎能带来理解世界的秩序感。但当秩序被打破,所有因素交织在一起时,有些现实便无可回避。
这场头发的谎言背后,谁是受益者?
H:这些事情似乎都隐藏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就像头发一样。我读书时,班上有一些非洲同学,他们都戴假发,还说很喜欢中国的假发。我从没想过这些头发的来源,直到和你聊过后,才意识到我的认知世界仿佛被照亮或坍塌,或者两者同时发生。
中国出口到非洲或美国的头发背后,还牵涉着国家政治的故事。我不知道你是否关注过当下中国假发和头发贸易的情况?
W:我对六十年代的一些推测,很多基于现有研究。方法论上,我仍在思考如何验证。毕竟,要找到六十年代所有史料来证明贸易存在并不容易,目前还没有特别决定性的证据。
但通过回忆录,以及当下的实地观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例如,安徽港集近几年仍悬挂“欢迎来到中国人发之乡”的横幅,工厂现代化,但当地人回忆,六十年代时家家户户就拿着秤、剪刀和尺四处收集头发,这个产业由此起步。
头发的研究不仅限于中国,印度在近几年的人类学研究做得也很深入。例如,2018年出版的 Waste of a Nation: Garbage and Growth in India 就将头发纳入垃圾回收体系研究,探讨贫困群体如何通过回收与出口实现再利用。2023年菲律宾出版的 Beauty Regimes 研究的范围更广,涉及美容产业与相关材料,包括头发。
H:今天准备这期节目时,我读到《人民日报》关于许昌假发的报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许昌发展为国内假发代工中心。改革开放后,许昌人抓住机会前往全国各地收购头发。”报道没有详细说明六十年代许昌如何成为代工中心,也没有提及代工对象和最终市场。但从官方口径来看,他们显然意识到了这件事。这也很可疑,当时中国几乎没人能买得起假发,也没有成熟的国内销售渠道,因此许昌成为代工中心,很可能服务于海外市场。
W:这种头发贸易本质上是国际贸易,必然涉及国家层面的参与,而非单靠小作坊或微型企业就能完成。围绕“谎言”思考时,我想到一个类似案例:八九十年代外国人在中国收养小孩。表面上,这似乎是善举,但实际上几乎构成跨国人口拐卖。
当时,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多余儿童要被拿走或缴纳罚款。这些孩子被集中送往收养机构,来自美国、西方等国的家庭顺利收养孩子,每个孩子都有详细文件,都有一个完美的悲惨身世,使收养者心安。直到近期,《纽约时报》的深度报道揭露,这些孩子大多被强行夺走,父母长期寻找未果,而收养者则出于善意。误会与谎言交织,酿成悲剧。
头发贸易可能不至于如此悲惨,但同样讽刺: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发现一个庞大体系在维持其运作。没有国家级参与,这种贸易几乎不可能成功。
H:如果是我想做这种生意,第一笔就会被抓。但若是国家做,同样的事可以做几十年无人问津。
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展开这个“谎言”,这种谎言的范式好像也在不断迭代,但同时又有很多相似性。就像大家觉得把头发剪掉是一个挺无辜的事儿;买的人觉得我只是买了个假发,为了变美,看起来也挺无辜的。但没有人去问,这整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变成了一个黑盒。
孤儿的问题可能不完全一样,因为夺取头发和夺取小孩毕竟不一样。夺取小孩当然更严重,那是一个生命。而收养的人其实大多是出于善意来的,并不是把这件事当成一种简单的消费行为。
W:我本意也不是要苛责谁,而是觉得正是这种反差带来一种极大的悲伤。那些外国人本以为自己在拯救生命、在行善,但其实无意中成了悲剧的一环。
头发的故事也是一样。那些中国女性以为自己在支持革命,而头发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它本身就带着层层递进的意义:服从、相信、剪去,这是一种身体的规训。头发最后却进入了一个完全消费主义的体系,那正是她们原本被教育要抵抗、要谴责的那一套关于“美”的这套话语,她们也在无意间成为其中的一环。
很多时候正是这种信息的不透明,让人们在一层层谎言之下,做着与自己本意完全相反的事。
文革是政治暴力的巅峰,也是身体控制的开始
H:虽然文革通常被视为政治暴力和荒谬的巅峰,但国家对身体的管控其实在文革之后变得更加强烈。如果把头发贸易作为起点,后续的计划生育政策、跨国收养,甚至九十年代河南的血灾事件,当地农民卖血导致的大规模艾滋病传播,其中也有地方政府的参与和鼓励,否则这些事件根本无法发生。类似情况还包括对器官移植、器官贩卖的指控。
在这些事件中,国家、社会与暴力的界限极其模糊:国家参与或默许,个体执行操作,受害者承受伤害。随着链条延伸,这种界限愈发模糊,最终责任落在社会身上。
尽管文革结束,政治暴力的高峰已过,但政治对个人身体的掌控非但没有减弱,反而似乎更为强烈。
W:其中还有一个透明度的问题。文革时期强调“直击灵魂”的服从与理念传递,但统治对象却并未获得完整信息,整个过程本质上是不公平的。
这种讽刺不仅存在于文革,也体现在跨国收养或头发贸易中:参与者的情感只是表面,而国家始终在其中获利,谁在获利?经济利益是理解这些事件不可忽视的一环。
H:
国家要直击你的灵魂,但是你不能去直击国家的灵魂。
W:这是一种完全不公平、不对等的状态。这类谎言和话语往往伴随所谓“崇高事业”,表面上大家都在努力,实际上有人在中间牟利,令人作呕。比如捐款赈灾,大家省吃俭用捐出善款,最终却发现这些钱根本没有流向真正需要的人。
大字报是官方的工具也是草根的自我书写
H:对很多人来说,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话题都相当沉重,也令人悲哀,因为它们本身都是问题。但我认为,做研究的责任就是去发现问题,而不是去歌颂世界的美好。对你而言,在日常研究中,你是如何寻找希望的呢?
W:我认为事物具有多面性。即便是在我研究大字报的过程中,也能看到希望。大字报常被视为自上而下的官方工具,但深入了解后,会发现其中也有草根的个人能动性。这给了我力量,也让我理解了自己为什么对大字报感兴趣。
在研究过程中,我的往事浮上心头。小时候搬到一个老小区时,曾被比我年长的邻居小孩欺负,当时孤立无援。愤怒的我就用油画棒在小区公共平台上写下欺负我的孩子的名字,写了“某某某是大坏蛋”。写完以后我就躲起来了,结果引发了一系列误会和冲突。我研究大字报最后的总结是,大字报从来不是孤立的纸张,而是一系列冲突的开端,一种在孤立无援时,能让人发声、寻求公道的方式。
后来在洛杉矶处理房东纠纷时,我有一刻非常愤怒,甚至想我要写一张大字报贴在楼里,告诉所有人这个房东怎么欺负我。虽然最后没有做这件事,但那种“我可以发声”的权利让我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力量。大字报就是纸和笔,你可以把我抓起来,但是我的纸依然贴在那里。
白纸革命等后来事件,也沿用了这种形式。
大字报在文革中可能是迫害工具,但形式被提炼出来,为疫情期间多少人们提供了一种反抗的可能。















![Abstract Narratives: Zao Wou-ki Exhibition Review [Re:locations]](https://static.wixstatic.com/media/68ad44_7c3470393ccc40d9b240e40c4f7d3114~mv2.png/v1/fill/w_980,h_724,al_c,q_90,usm_0.66_1.00_0.01,enc_avif,quality_auto/68ad44_7c3470393ccc40d9b240e40c4f7d3114~mv2.png)
Comments